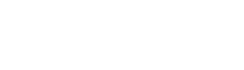6月20日,是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原华东水利学院创始人之一徐芝纶院士诞辰100周年。6月21日,《中国水利报》以《新中国一代力学宗师》为题刊发了纪念徐芝纶院士百年诞辰的文章。全文如下:
新中国一代力学宗师
――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河海大学教授徐芝纶百年诞辰
河海大学工程馆前的广场上,鲜花簇拥的徐芝纶院士的铜像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熠熠生辉。
今年6月20日,是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原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副院长、河海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党员徐芝纶先生的百年诞辰。
英风俊彦 潜心向学
徐芝纶,字君素,江苏省江都县(今江都市)人,1911年6月20日出生于邵伯镇。1930年,徐芝纶考取清华大学土木系土木专业。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留校。翌年他与钱学森、张光斗一起考取留美公费生。
在美国的第一年,徐芝纶读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水力发电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他负重致远,门门功课全是A,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然后又用一年时间师从著名权威、哈佛大学威士加德教授学习弹性力学,获得工程科学硕士学位。他怀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两次谢绝麻省恩师希望他留校工作、并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提供最高数额奖学金的盛情,决意启程,奔赴国难。
1937年8月初,26岁的热血青年徐芝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艰难困苦 蔽日干云
抗战时期,徐芝纶执教的浙江大学被迫3年6迁。每次搬家,都是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日寇追兵。到了一处,就在祠庙里或搭草棚子上课,白天随便找些东西充饥,晚上铺了稻草在地上睡觉。由于缺乏教师,徐芝纶教过十几门课程。正是这样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环境,使他的思想、意志、心理经受了不同寻常的磨砺。
1943年,徐芝纶应聘到重庆资源委员会水利勘察总队,主持水电工程开发设计工作,还与美国垦务局来华专家萨凡奇合作,进行长江三峡枢纽的初步设计。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任教授,1948年交大新建水利系,他又转任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他还兼做中大土木系教授,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授,私立之江大学上海分校教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当年在上海求学,都曾做过徐芝纶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芝纶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1952年,汇聚全国10多所高校水利系科的高等学府华东水利学院在南京建立。徐芝纶愉快接受组织安排,举家迁到南京。他是学院筹建委员会8名委员之一,同时担任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和管理工作。1954年,徐芝纶任学院教务长,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学院副院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业绩,1960年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赴京参加群英会;1978年获评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理事长和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徐芝纶毕生心系祖国,向往光明。他于1955年经著名港工专家严恺教授介绍加入九三学社,担任过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常委;1960年和1980年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80年6月16日,徐芝纶以69岁高龄光荣入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教学艺术 炉火纯青
徐芝纶课堂讲授质量之高,在业界早已享有盛誉。凡是听过他的课或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所授内容的严密逻辑、清晰概念、科学推理和高超艺术所折服。
他在讲解基本理论的同时,还把思路、方法、对内容的评价和存在的问题交给学生,启发学生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学生听他的课兴趣盎然,是高水平的艺术享受。工科学生对比较艰深的弹性力学课程,反而感到易学易懂。
徐芝纶在撰写的论文《怎样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中,总结了8个方面的教学经验,在全国众多高校中引起极大反响和高度评价,甚至被奉若圭臬。《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还配发评论员文章《提高教学质量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强调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倡议所有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师都要向徐芝纶教授学习,刻苦研究教学方法,把真知灼见传授给学生。
学科大观 灼灼其华
徐芝纶是中国力学学科在当代发展过程中的领军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他的名字甚至成为学科高度的一个符号,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
有限单元法是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才定名并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家正值“文革”,几乎无人顾及,但徐芝纶敏锐地觉察到有限元这个新生事物的巨大学术价值和在水利、土建工程中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国内率先引进、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于197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相关专著《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方法让中国人重新跻身于学科前沿,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其成果获评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内第一次真刀真枪地用有限单元法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成果《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1985年获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其后他和同事们参与了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南水北调、润扬大桥等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利等工程中相关项目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一大批关键力学难题,获得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笔耕不辍 仰屋著书
徐芝纶先后出版编著、专著11种15册,译著6种7册,形成了多层次、多专业、多方位、广泛适用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其中《弹性力学》第一版获评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第二版获评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弹性力学简明教程》被作为全国工科院校通用教材广泛采用;《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是我国第一部有限单元法专著,在国内起到了开拓、引领学科的重大作用。
徐芝纶的多部著作一版再版,至今每年仍在重印,总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成为永恒的经典。国外众多高校图书馆也收藏有徐版图书,而且是读者借阅使用频率很高的图书之一。
行仁倡义 高风亮节
徐芝纶一辈子崇尚正义,崇尚民主,崇尚科学。关于做人,他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1995年11月,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做人有三种境界:一是大公无私,二是先公后私,三是假公济私。第一种是理想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必须努力追求达到;第二种是普遍的、通常的、有德性的境界,但是要努力抑私而扬公,小私而大公,切不可公私扯平甚至大私而小公;第三种是禁区,做人入了禁区,也就没有人品人格可言了。
教书育人60年,徐芝纶教过的学生已达数千人。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带研究生,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博士,包括全国第一个水工专业博士,弟子们早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4人。
徐芝纶夫妇一生膝下无子女,他们给予青年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是父母般的关爱。三年困难时期,徐芝纶经常把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请到家中,让老伴给年轻人烧些荤菜补充点油水;“文革”中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他经常自掏腰包买来副食品让师生打打牙祭;平时哪个同事生活困难或生病住院,他知道后一定会带一笔钱或买上水果前往看望慰问,哪个年轻人结婚,他也一定会带着礼物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徐芝纶写书得到的稿酬,绝大部分捐给了学校以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他还拿出20万元积蓄参与设立“徐芝纶教育基金”(徐芝纶病逝后,夫人伍玉贤遵从其遗愿,又向基金捐款25万元),用于激励青年教师和学生积极向上、奋发成才。而他自己一生安贫乐教,生活俭朴,一把计算尺从留学美国一直用到1970年,几件家具还是20世纪50年代从上海调到南京时购置的,使用数十年从未更换过。他病重住院期间,连一件好点的衬衫也没有,甚至在他病逝时,家中柜子里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
徐芝纶先生是一本大书,一页页翻过,犹如片片花落心河。
新中国一代力学宗师
――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河海大学教授徐芝纶百年诞辰
河海大学工程馆前的广场上,鲜花簇拥的徐芝纶院士的铜像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熠熠生辉。
今年6月20日,是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原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副院长、河海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党员徐芝纶先生的百年诞辰。
英风俊彦 潜心向学
徐芝纶,字君素,江苏省江都县(今江都市)人,1911年6月20日出生于邵伯镇。1930年,徐芝纶考取清华大学土木系土木专业。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留校。翌年他与钱学森、张光斗一起考取留美公费生。
在美国的第一年,徐芝纶读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水力发电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他负重致远,门门功课全是A,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然后又用一年时间师从著名权威、哈佛大学威士加德教授学习弹性力学,获得工程科学硕士学位。他怀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两次谢绝麻省恩师希望他留校工作、并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提供最高数额奖学金的盛情,决意启程,奔赴国难。
1937年8月初,26岁的热血青年徐芝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艰难困苦 蔽日干云
抗战时期,徐芝纶执教的浙江大学被迫3年6迁。每次搬家,都是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日寇追兵。到了一处,就在祠庙里或搭草棚子上课,白天随便找些东西充饥,晚上铺了稻草在地上睡觉。由于缺乏教师,徐芝纶教过十几门课程。正是这样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环境,使他的思想、意志、心理经受了不同寻常的磨砺。
1943年,徐芝纶应聘到重庆资源委员会水利勘察总队,主持水电工程开发设计工作,还与美国垦务局来华专家萨凡奇合作,进行长江三峡枢纽的初步设计。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任教授,1948年交大新建水利系,他又转任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他还兼做中大土木系教授,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授,私立之江大学上海分校教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当年在上海求学,都曾做过徐芝纶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芝纶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1952年,汇聚全国10多所高校水利系科的高等学府华东水利学院在南京建立。徐芝纶愉快接受组织安排,举家迁到南京。他是学院筹建委员会8名委员之一,同时担任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和管理工作。1954年,徐芝纶任学院教务长,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学院副院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业绩,1960年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赴京参加群英会;1978年获评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理事长和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徐芝纶毕生心系祖国,向往光明。他于1955年经著名港工专家严恺教授介绍加入九三学社,担任过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常委;1960年和1980年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80年6月16日,徐芝纶以69岁高龄光荣入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教学艺术 炉火纯青
徐芝纶课堂讲授质量之高,在业界早已享有盛誉。凡是听过他的课或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所授内容的严密逻辑、清晰概念、科学推理和高超艺术所折服。
他在讲解基本理论的同时,还把思路、方法、对内容的评价和存在的问题交给学生,启发学生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学生听他的课兴趣盎然,是高水平的艺术享受。工科学生对比较艰深的弹性力学课程,反而感到易学易懂。
徐芝纶在撰写的论文《怎样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中,总结了8个方面的教学经验,在全国众多高校中引起极大反响和高度评价,甚至被奉若圭臬。《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还配发评论员文章《提高教学质量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强调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倡议所有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师都要向徐芝纶教授学习,刻苦研究教学方法,把真知灼见传授给学生。
学科大观 灼灼其华
徐芝纶是中国力学学科在当代发展过程中的领军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他的名字甚至成为学科高度的一个符号,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
有限单元法是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才定名并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家正值“文革”,几乎无人顾及,但徐芝纶敏锐地觉察到有限元这个新生事物的巨大学术价值和在水利、土建工程中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国内率先引进、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于197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相关专著《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方法让中国人重新跻身于学科前沿,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其成果获评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内第一次真刀真枪地用有限单元法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成果《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1985年获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其后他和同事们参与了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南水北调、润扬大桥等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利等工程中相关项目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一大批关键力学难题,获得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笔耕不辍 仰屋著书
徐芝纶先后出版编著、专著11种15册,译著6种7册,形成了多层次、多专业、多方位、广泛适用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其中《弹性力学》第一版获评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第二版获评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弹性力学简明教程》被作为全国工科院校通用教材广泛采用;《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是我国第一部有限单元法专著,在国内起到了开拓、引领学科的重大作用。
徐芝纶的多部著作一版再版,至今每年仍在重印,总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成为永恒的经典。国外众多高校图书馆也收藏有徐版图书,而且是读者借阅使用频率很高的图书之一。
行仁倡义 高风亮节
徐芝纶一辈子崇尚正义,崇尚民主,崇尚科学。关于做人,他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1995年11月,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做人有三种境界:一是大公无私,二是先公后私,三是假公济私。第一种是理想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必须努力追求达到;第二种是普遍的、通常的、有德性的境界,但是要努力抑私而扬公,小私而大公,切不可公私扯平甚至大私而小公;第三种是禁区,做人入了禁区,也就没有人品人格可言了。
教书育人60年,徐芝纶教过的学生已达数千人。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带研究生,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博士,包括全国第一个水工专业博士,弟子们早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4人。
徐芝纶夫妇一生膝下无子女,他们给予青年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是父母般的关爱。三年困难时期,徐芝纶经常把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请到家中,让老伴给年轻人烧些荤菜补充点油水;“文革”中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他经常自掏腰包买来副食品让师生打打牙祭;平时哪个同事生活困难或生病住院,他知道后一定会带一笔钱或买上水果前往看望慰问,哪个年轻人结婚,他也一定会带着礼物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徐芝纶写书得到的稿酬,绝大部分捐给了学校以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他还拿出20万元积蓄参与设立“徐芝纶教育基金”(徐芝纶病逝后,夫人伍玉贤遵从其遗愿,又向基金捐款25万元),用于激励青年教师和学生积极向上、奋发成才。而他自己一生安贫乐教,生活俭朴,一把计算尺从留学美国一直用到1970年,几件家具还是20世纪50年代从上海调到南京时购置的,使用数十年从未更换过。他病重住院期间,连一件好点的衬衫也没有,甚至在他病逝时,家中柜子里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
徐芝纶先生是一本大书,一页页翻过,犹如片片花落心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