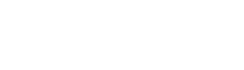2005年10月27日,是河海大学90华诞纪念日,学校将举办隆重的庆典活动,校庆筹备委员会宣传组的同志约我写点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写下点什么,因为十分巧合的是,2005年10月27日也是我到河海大学报到10周年的纪念日!而且10年前的10月27日,我一报到就投入到紧张的8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中(那年的庆祝大会等主要活动因故推迟到11月2日举行),当年场景犹在昨日,光阴飞逝已过10载,如今又在为90周年校庆忙乎。但是写什么呢?提起笔却又踌躇再三,写河海的历史自己资历太浅,写学校的发展个人能力有限,写校庆的感受又觉笔拙词穷,目光游移中看到玻璃台板下我与一位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的老人的合影,由此又想起三年前的一件趣事,略一思索,就先写下了一个题目----《我家五代河海人》。
2002年春,我参加了河海大学纪念华东水利学院成立50周年的筹备工作。在一次讨论庆祝活动内容的筹备组会议上,一位教管理并以策划大型活动见长的老师说,如有既参与创建“华水”又是祖孙三代“河海人”的一个家庭在庆祝大会上亮个相,演个节目也行,致个辞也行,如各人再有点“事迹”介绍一下就更好,一定很能调动气氛、激动人心,可惜学校里两代的好找,三代的恐怕就找不到了。话音刚落,大家就大笑起来,他有点莫名其妙,连声问:“我说得不对吗?这绝对是个好主意!我甚至连这个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薪火传承’”。大家边笑边指着我说:“不是笑你主意不好,不用找,坐你旁边的就是三代‘河海人’,而且完全符合你‘参与创建华水’和‘各人都有点事迹’的要求”。
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家决定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水利系科汇聚南京,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华东水利学院。于是,我的父母从钱塘江畔来到扬子江边,从此全家就在南京扎了根,“华水”也成了我儿时的乐园。父亲当年以优异的成绩于美国伊里诺依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该校以土木工程著称于世,在2001年美国著名大学学科排名中伊里诺依大学的土木工程仍为全美第一),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得知解放军已打过长江、新中国即将建立,遂谢绝校方及导师挽留,毅然回国投身建设。父亲回国后在他所从事的岩土工程教学和科研中多有建树: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土力学教材《土壤力学》;于上世纪60年代发表并推广的Lee法,为流变土体的固结提出了创新的方法,从而被国内外学术界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了该方法;主编的研究生教材《土工原理与计算》、本科生教材《土力学》分别于1987年和1992年获得水利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主持或参与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部、省级以上奖励,其中“土质防渗体高土石坝研究”、“小浪底土石坝震后永久变形”分别获1993年和199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交换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编委、《岩土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和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作为中国唯一专家入选国际土力学学会组建的海岸岩土工程委员会并被确定为核心组成员;培养的学生已成为水利、交通、土木、高教等行业很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父亲的学术地位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公认,曾多次应邀赴德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持人或特邀报告人;父亲的为人也一直为校友、同事所称道。母亲则在教学管理岗位上勤恳工作。两人一直在“河海”工作到离休和退休。
1995年秋,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再次走进河海校园。时隔数十年,道路、山岗依旧但面貌大变,然而更按捺不住的是内心的激动,因为我也成了“河海人”中的一员。对“河海”的热爱也成为我工作的动力,10年来13次受到学校党委、行政和江苏省委教育工委的表彰与奖励,1998年、2001年被评为河海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01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2000年夏,儿子高中毕业,符合免试保送条件的他也选择了河海大学。儿子进校不久,就连获军训积极分子和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先后担任班委和年级学生工作组副组长。2001年刚升入二年级就在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电脑网络大赛中战胜众多研究生及高年级学生,一举获得电脑技能竞赛特等奖和软件展示三等奖,并获得免试保送研究生资格。大学期间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因此,我家是名副其实的三代“河海人”。
但是,我家与“河海”的缘分还不止三代!我父亲还不是我家第一代“河海人”,我父亲的表叔沈百先不仅是我家、也是我国第一代“河海人”。
沈百先,名在善,是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立后招收的首批正科学生(见河海大学1995年出版的《河海大学人名录》)。1919年毕业后即投身水利建设与教育,先后就职于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水利工程处、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水利工程处、河海工科大学、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中央大学水利系等单位,其间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代理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土木工程系主任等。1931年4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沈百先被推选为学会董事(会长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首任教务长李仪祉),并连任至六届;1941年在七届学会上当选为会长,并连任至九届。1945年6月,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改组为水利部,沈百先被任命为水利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水利工程学会副会长。同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向中国归还宝岛台湾,沈百先被国民政府派往台湾接收水利事业。后任台湾中原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台湾大学教授,编著出版了《中华水利史》、《水利工程名词》等书籍,为祖国的水利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晚年定居美国。
我没有见过沈百先,但却感受过他对“河海”的眷恋之情。2002年夏,校长办公室负责校友联系工作的同志到我办公室,说一位美国来的老先生要见我。见面后,老先生自我介绍名叫沈平先,这次回国专程来河海大学,是替家兄沈百先还愿的,他是“老河海”的毕业生并曾在母校任教多年,一直想回母校看看同时也看望你们却未能实现。“见到你非常高兴,论辈分你得叫我叔公!来不及到你家去了,一定代我向全家问好!”临离校时,老人还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在办公楼前拍下了玻璃台板下的那张照片。
还是2002年夏,一位“论辈分得叫我叔公”的后生在高考中考进了河海大学,成为我家第五代“河海人”!
我家五代“河海人”,而且与 “老河海”的创建、与“老河海”在共和国的新生密切相关,这种情况恐怕在全国的高校、全国的水利单位甚至其他单位也不多见,我想。也因此在参加学校举办的教职工书画展时,我心血来潮、附庸风雅地去刻了一枚闲章----“河海人”。
后记:在纪念河海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兼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钱家欢、叔公沈百先;河海大学为纪念父亲在岩土工程学科以及学校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在校内设立了“钱家欢岩土工程奖学金”,亦以此文表达对学校的感激与感谢。
钱恂熊
(作者为河海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常委会秘书、保密委办公室主任)